 首页
首页-
本所概况
哲学所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是我国哲学学科的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历任所长为潘梓年、许立群、邢贲思、汝信(兼)、陈筠泉、李景源、谢地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全国没有专门的哲学研究机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 <详情>
- 党建工作
- 研究学人
- 科研工作
- 学术期刊
- 人才培养
博士后更多+
- 图书档案
图书馆简介

哲学专业书库的前身是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与哲学研究所同时成立于1955年。1994年底,院所图书馆合并之后将其划为哲学所自管库,从此只保留图书借阅流通业务,不再购进新书。
2009年1月16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哲学专业书库正式挂牌。
<详情> - 哲学系
【王齐】求真寻美之路——汝信先生的学术人生
1993年初,当我以中文系文艺美学研究生身份紧张备考汝信先生“西方的哲学与美学”博士生的时候,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就读的学兄寄来一份题为《学者·战士》的复印材料,叮嘱我“用心一读”。这是某杂志“当代学人剪影”栏目介绍汝信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的文章,署名“忍言”。标题旁有一幅汝信漫画头像,漆黑微锁的双眉,为柔和的面部增添了一丝坚毅神情。那时,我已读过一些汝信关于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论著,对那本具有“美学散步”风格的《美的找寻》情有独钟,而《学者·战士》一文让我首次认识了理论论著背后的人。一位在上海长大并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青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弃笔从戎,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洗礼,最终在哲学研究当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本,他还有一段从事行政管理十七载的经历。如此丰富的阅历中有着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那就是对真理和美的追寻。
科学与民主之路
1931年,汝信出生在上海一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开明家庭。父亲毕业于著名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后在上海租界地工部局任律师;母亲毕业于“东南体专”,是中国最早专攻体育专业的女性之一,毕业后曾在中学教授体育和语文,后为专心照顾子女放弃心爱的体育教育工作,回归家庭。汝信从小即受到良好的现代教育,4岁进美国教会办的中西女中,从幼稚园到小学共读了两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汝信被迫中断学校教育,跟哥哥姐姐一起在家接受了一段中西合璧的教育。父母除了请来教授英语和数学的老师外,还请了父亲当年在吴江的塾师、一位严厉的晚清秀才教文言文和一位脾气暴躁的女教师教钢琴。汝信直言厌恶那段琴童生活,但早年的音乐教育在他的心灵中播撒下一颗喜爱艺术和美的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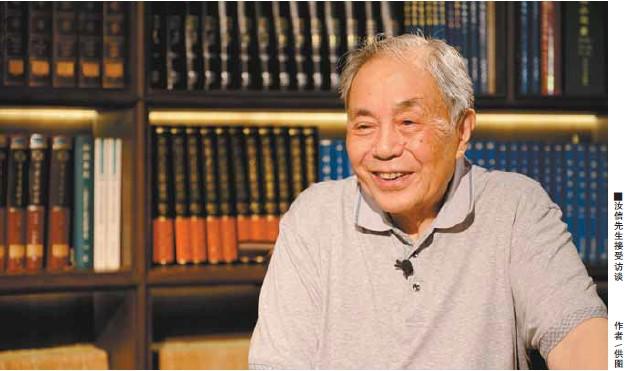
1941年,汝信结束了家庭教育,先在圣公会创办的桃坞中学读初中,三年后直升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高中。这段时间,汝信有机会了解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亲身感受到了民众的爱国激情。两所中学虽是教会学校,但奉行自由和宽容政策,不强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正是在这种宽松的教育环境下,汝信开始大量阅读中外文学作品,鲁迅的《呐喊》《彷徨》和《野草》,巴金的《家》和《灭亡》,易卜生的《娜拉》和《国民公敌》,以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的作品都是他所喜爱的,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种子开始萌芽。
1945年抗战结束时,14岁的汝信提前结束高中学习,进入圣约翰大学,主修政治学,副修经济学。圣约翰大学除了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用中文教授之外,其余课程一律用英文讲授,包括“三民主义”,因此为汝信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大学期间,汝信受到学生组织的各项活动和“要民主,要自由”的学生运动的强烈吸引,追求进步,他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读书联谊会”活动,接触到了苏联的进步文艺作品和社科作品,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因“苏联情结”开始在家中跟流亡上海的白俄学习俄文。1948年12月,汝信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圣约翰大学根据学分修习情况颁发毕业证,年仅18岁的汝信提前大学毕业。回顾这段求学经历时,汝信总说自己当年因为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没有认真读书。若按和平年代的标准,可能如此;不过这段求学经历的意义在于,汝信一直是走在“五四”科学与民主的道路之上的,对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使得他从来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型学者,而是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学人。
大学毕业后,汝信如愿加入了解放军第九兵团,成为政治部民运部的一名干事,在上海解放初期做了许多协调军民关系的工作。1950年11月7日,汝信随第九兵团跨过鸭绿江,实现了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想在战争中锻炼自己的愿望。随着战争的进程,“阵地战”开始,汝信在司令部做英文翻译,中间挤出了一点时间,断断续续地阅读随身携带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1956年汝信在《文史哲》上发表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以及1958年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美学的批判》,当是在朝鲜战场上读书的结果。
1955年汝信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部,从事行政工作,主要组织科研人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另一项工作是参照苏联副博士制度建立中国的研究生制度。在参与起草学位制条例的时候,汝信萌生了从事哲学研究的念头,并于1956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贺麟学习黑格尔哲学。贺先生要求汝信系统阅读从古希腊到黑格尔的主要西方哲学名著,并要求他边阅读边翻译。在贺先生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之下,汝信很快成长为西方哲学研究领域的新秀,走上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路。
求真之路
改革开放前的西方哲学研究主要围绕哲学史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展开,当时对“黑格尔之后”的哲学亦有所研究,不过是为批判之故而将其当成反面教材,汝信的工作亦不例外。真正开始科学的西方哲学研究,当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黑格尔研究仍是重点,所不同在于,之前的黑格尔研究主要围绕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展开,集中在从康德、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的思想线索之上,对黑格尔哲学本身的研究不够深入。随着时代的变迁,汝信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性,并且首先关注到青年黑格尔的异化思想,于1978年连续发表了《青年黑格尔的社会政治思想》和《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两篇文章。黑格尔哲学对汝信这一代学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因为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渊源关系,还因黑格尔作为西方思辨哲学体系的高峰所具有的包罗万象的气势和广阔的历史视野,更因为黑格尔辩证法思想能够克服现实中常常出现的教条化和简单化的思想倾向。
在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同时,汝信还把思考的目光投向历史。1980年8月15日,汝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反思和批判新中国成立以来把人道主义当作修正主义进行批判的错误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最关心的就是人的问题,因此“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必不可少的因素”。这篇文章不仅为人道主义正名,还从深远的意义上对学术界泛政治化和乱扣帽子的错误进行了批判,为理论研究的合法性扫清了障碍,开思想界拨乱反正之先河。后来,这篇文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引起了一些讨论,但汝信在内心里从未改变对人道主义的认识。在1992年首版的《美的找寻》中题为《〈天鹅湖〉的悲剧结尾和莎乐美的爱》一文中,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主题再次回响。汝信明确指出,恰恰因为在过去的哲学和美学研究中不谈人的问题,留下了理论空白,反给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学说以机会。“马克思主义如果要真正进入人们心灵深处,成为生活的指导,那就不仅要解决社会发展问题,而且要回答使人们感到困惑的切身的个人问题,包括对爱与死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有待于我们作出巨大努力的一个新的宽广的领域。”这些反思和批判意义重大,历史证明,汝信的认识是正确的。
1981年,汝信被中国社会科学院选派到哈佛大学作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由著名哲学家普特南接待。因从小在美国教会学校学习,汝信对西方文化并不感到特别陌生,但对居美国哲学界主流地位的分析哲学却很陌生,感觉不具备对话的可能。在与国外学者交流之后,汝信决定利用哈佛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和丰富的藏书,有意识地关注“黑格尔之后”除马克思哲学之外的另一条注重个体生存的思想线索,开始研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使我们睁开了眼睛”的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哲学思想。1982年,汝信撰写了《克尔凯郭尔思想述评》,这篇文章直到1985年才发表在《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8卷,这是国内第一篇全面反映克尔凯郭尔哲学思想的作品。自1982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汝信还抽时间陆续撰写了其他研究克尔凯郭尔的论文,2008年以《看哪,克尔凯郭尔这个人》为题出版。这本书是汝信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与克尔凯郭尔进行的对话。
汝信对尼采的研究同样较早。1985年,《论尼采悲剧理论的起源——关于〈悲剧的诞生〉一书的研究札记之一》发表在《外国美学》第1辑,而综合性更强的论文《尼采的美学与文艺思想》则于1988年发表于《红旗》杂志。
汝信的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研究不仅开始早,而且从一开始他就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汝信曾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克尔凯郭尔,也不希望别人走克尔凯郭尔由对生活的悲观绝望最终倒向上帝的道路。对于尼采,汝信则不懈地揭示其思想中的矛盾,他曾在一篇书序中写到,“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只有弱者才需要辩护,而尼采却决不是弱者。他所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理解”。汝信坚持认为,学术研究是一项科学事业,而非成为被研究对象的信徒或吹鼓手。我最早提交的以克尔凯郭尔为题的博士论文第一章被先生彻底否定,理由是我完全被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和文字风格所俘获,缺乏“批判的态度”。这句“批判的态度”适时地点醒了我,成为我治学的起点。
寻美之路
汝信是学界公认的美学家,虽然他常常自谦,说自己不是“专门研究美学的专家,只能算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早在1963年,汝信就出版了美学论文集《西方美学史论丛》。在这本汝信自认的“习作集”当中,他对普罗提诺的研究非常值得一提。在那个年代,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中世纪仍然背负着“黑暗时代”的恶名,但汝信凭借高度的学术敏感,不相信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会在思想上毫无建树。在资料奇缺的情况下,他通过美学史资料中收录的普罗提诺著作的英译本和其他零散资料,撰写了《普罗提诺论美——新柏拉图派美学初探》一文,展示出了学术的前瞻性。20年后,汝信出版了第二本美学论文集《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展现出了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美学到中世纪的普罗提诺,从德法启蒙运动时期的莱辛和狄德罗,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的康德、黑格尔、谢林,西方美学史上关键时期和重点人物的思想先后成为汝信的研究对象。改革开放后,汝信还从尼采美学出发,顺着西方非理性主义的线索,对现代美学中的无意识问题进行了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西方美学的古今发展线索。

在从事西方美学史研究20余年间,《大希庇阿斯篇》结尾中苏格拉底所说的“美是难的”的命题,以及歌德“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的名言一直萦绕在汝信的心头。汝信认识到,美学史研究要想深入,离不开哲学史研究,更离不开艺术;美学研究应避免走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道路,而应转向艺术王国,直接面对人类的艺术创造。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汝信有机会出国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参观了不少欧洲知名艺术馆、博物馆,也欣赏到了高水平艺术团体的表演,但他没有止步于对艺术作品的陶醉和感动之中,而是凭借多年哲学和美学研究的功力,对个体的艺术感受进行理论升华。在《〈吃土豆的人〉的启示》一文中,汝信描写了在阿姆斯特丹看到梵高名画《吃土豆的人》时受到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他发现梵高画中体现的不是“令人愉快的美”,而是“一种看了使人直想流泪的美,令人难以忍受的美,叫人喘不过气来的美”。由这种直观感受出发,汝信进一步围绕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个体在现代社会的异化问题等进行反思,这篇文章堪称具有哲学高度的美学和艺术研究之典范。
1998年汝信卸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他把更多时间投入到世界文明比较研究当中,希望通过对不同文明的了解和互鉴,制定出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文明建设又能有效应对外来文明挑战的战略。他领衔主编出版的“世界文明大系”和“世界文明通论”多卷册著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这时期汝信对美学的探索停止了吗?没有。2019年,汝信发表了人生第一部中篇小说《一个人的初恋》。小说取材于抗美援朝战争,是一部青春回忆和战争反思紧密交织的作品,结构则是向苏联作家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致敬的结果。小说刊发在《人民文学》第8期“军旅文学专号”上,很快就被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小说选刊》2019年第9期转载,后来又被收入中国作协创研部编选的《2019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对于首次创作小说的汝信来说,这个成功来得有些突然;但对于从事哲学和美学研究60余载的学者来讲,一切似乎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汝信在北京郊区生活一年多,只能通过电话与外界联系。这中间我曾把自己看到的一些文学艺术类图书快递给他,如《名画在左科学在右》《余下只有噪音:聆听20世纪》等,每次先生都会兴味十足地阅读。2021年春节前,我从凤凰文库“艺术理论研究”译丛中挑了著名艺术史家夏皮罗的《现代艺术:19与20世纪》。几天后,汝信先生打来电话交流心得,并且告诉我,多年前他是读过这书的英文版的。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2021.5.1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邮编:100732
![]() 电话:(010)85195506
电话:(010)85195506
![]() 传真:(010)65137826
传真:(010)65137826
![]() E-mail:philosophy@cass.org.cn
E-mail:philosophy@cass.org.cn















 潘梓年
潘梓年 金岳霖
金岳霖 贺麟
贺麟 杜任之
杜任之 容肇祖
容肇祖 沈有鼎
沈有鼎 巫白慧
巫白慧 杨一之
杨一之 徐崇温
徐崇温 陈筠泉
陈筠泉 姚介厚
姚介厚 李景源
李景源 赵汀阳
赵汀阳












